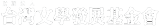追夢少年的起點——從文學到政治,再從政治到台灣歷史
我回台灣的第一份工作,是在民進黨擔任文宣部主任,一待就三年。不過,後來體會到,在政治的場合裡,永遠只有輸贏,勝選的一方代表道德,落敗就淪為不道德者。人們完全不管政治人物用什麼樣的手段、方式勝選,只看結果。因此,我開始覺悟這樣的場域不適合我繼續待下去,不適合作為追求人生之夢的道路。
人生永遠無可預知,年少時候,我們都曾經作過無數個夢。大學時期,我研究宋代歷史,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轉向研究文學;當我回歸到文學之路時,竟然可以從最偏遠的小鎮──沙鹿的靜宜大學,漂流到暨南大學,最後到政治大學,這一條道路是我在海外流亡時沒有想過的。當初出國,只是想拿博士學位回來,一輩子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黑名單,必須在國外停留十幾年才能歸來。這種飄泊的滋味,我嚐得非常辛苦,必須把親情、友情都斬斷,過去所有的夢也跟著被切斷。即使如此,我仍然相信只要保留一點點希望,在內心持續燃燒,即使希望非常微小,也能找到媒介一直燃燒下去。
在台灣的時候,我是一個寫詩少年,一九七○年成立龍族詩社,發行《龍族詩刊》,總共維持了四、五年。這本詩刊,在整個文學史上可能沒有幾個人會記得,但是它擔負一個重要的任務,就是發動了新詩論戰,開始批判現代主義。我最初對現代詩產生批判,也是跟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:一九六久年之前,台灣以中華民國之名,代表整個中國;但是,進入一九七○年以後,整個局勢就不同了;當年我正在台大讀歷史研究所,白天讀宋代歷史,晚上寫現代詩,整個台灣社會被關在我的思考之外。同年,發生釣魚台事件,美國粗暴地將釣魚台主權轉移給日本;台灣漁民從清代以降就開始捕魚的海域,竟然在一九七○年,只因美國將太平洋巡防任務交給日本時,在地圖上將釣魚台直接劃進日本的巡防區域,使得這個問題直至今日,還爭論不休。不久後,「釣魚台運動」形成,先從海外留學生開始,一路燒回台灣。作為一個研究十二世紀中國的台大研究生,從來沒有想過二十世紀的台灣會發生什麼變化;也因為這個事件,我終於還是走出研究室、書房,開始關心台灣社會,才知道那時候整個台灣的大學生,都投入這場運動。
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,政治跟我的關係是什麼?
一九七一年,台灣被趕出聯合國,從此喪失國際地位,四十年過去了,直到今天,我們還在面對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問題。對我來說,這是一個很大的打擊:「如果台灣不能代表中國,請問台灣代表什麼?」作為一個研究歷史的讀書人,我開始這樣問自己。一九七二年,尼克森到北京與毛澤東見面, 同年二月二十八日, 與周恩來訂定《上海公報》,從那時候我就已經感受到,歷史正在轉換。於是,我開始思考,自己寫如此衰弱的詩行,能夠挽救台灣嗎?把自己投入詩的想像中,將自己燒得很旺盛,卻完全不能夠拯救、改變台灣的命運。《上海公報》最大的效應,即是所有友邦看到美國轉向,紛紛跟台灣斷交,該年,我眼見台灣從一百多個建交國,到最後所剩無幾。
這種失去的滋味,在生命中體會得最劇烈的時刻,是我在美國求學的那段時期。有一年,聖誕節前夕與幾個朋友約好,坐車到溫哥華,開車的是日本人,同車朋友分別是印度人、韓國人與菲律賓人,到了美加邊境的時候,開始落雪;我平生第一次看到雪景,好美,忍不住讚嘆美國真是一個漂亮的國家。車子進入入境關口,加拿大官員要求我們交出護照驗明身分,朋友們一一通過,海關官員卻看著我的護照,告訴我加拿大不承認這本護照。當別人不承認你是一個國家時,
我才真真切切體會到斷交的滋味為何。最後,僵持不下,位階較高的官員問我與同車朋友的關係,我回答:「我們都是華盛頓大學的同學,只是想來看看加拿大的景色。」於是,官員請我拿出學生證,並且在表格上填華盛頓大學的學生證
號碼。那一刻,意識到台灣護照竟然輸給美國大學的學生證,我開始問自己:「家國究竟在何方?」我想,一個人會有政治覺醒,並非因為你是泱泱大國的國民,而是個人命運受到干涉的時候。你可以不理政治,但總有一天它會來理你。也是在這種情況下,我回到西雅圖,開始覺得自己在台灣長大,完成教育,卻從來不知道台灣的歷史與命運為何,是一件可恥的事。
於是,從那時候開始,夜裡我研究台灣歷史,搜集台灣文學來閱讀。這一段蒼白、黯淡的留學生活,在最初的幾年,完全沒有想過這樣的經歷,會在往後與自己的命運息息相關。
從歷史出發,面向當代
最初讀台灣史,是在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館大量搜集資料。美國大學對歷史資料保存相當好,特別是華盛頓大學,在一九五○至一九七○年冷戰時期扮演美國白宮的智庫,所有遠東政策都會請教華盛頓大學教授,因此圖書收藏非常完整。我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下,進行大量的台灣歷史文獻閱讀。
閱讀的過程中,經常有一些奇妙的經驗。華大圖書館書籍陳列的分類,台灣一類,中國大陸一類。但在一次檢視書籍時,發現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書籍放在一起,一本是台灣出版的《民族救星蔣總統》,另一本是大陸出版的《雙手沾滿鮮血的蔣介石》,兩造對比,使我嚇了一大跳。第二年,也就是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,蔣介石去世,我在《中央日報》上讀到「我們的蔣總統昨日薨」,「薨」是古代對皇帝駕崩的尊稱。隔日,《人民日報》登了一則很小的消息,標題為:「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蔣介石,昨天死了」,如此簡單。在這種強烈比較之下,我開始覺悟歷史是如何寫出來的?是誰在寫歷史?誰有權力,誰就擁有發言權,而你是什麼立場,就用什麼立場的語言來表達。另外,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漢奸秦檜。研究漢奸有一個困難,即是大部分的史料都被燒掉,只能從別人片段的註解揀取。研究秦檜的另一個發現,則是體認到歷史就是「成者王,敗者寇」,如果秦檜繼續活下去,沒有失利的話,也許在整個中國歷史上的評價會翻轉。這幾
點體驗,都讓我開始對歷史產生懷疑。
其實,我想要強調的是,人類的智慧是有限的,我們可以知道過去發生的事,卻永遠無法預知未來;而對未來的不可知,使我在研究文學時,感到更加的惆悵。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,台灣開始被美軍轟炸,在那之前,台灣沒有人相信日本會敗給美國。也就是在那個時候,台灣作家被指示應該寫歌頌戰爭、歌頌大東亞的小說,大家開始很認真的朝這個方向創作。但是,沒有想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日本投降,整個台灣人也都跟著悲痛、投降,林文月的散文中,就寫到了這一段舉國悲慟的歷史氛圍。在皇民化運動中,全台灣的男丁都跟著到前線作戰,作家如果不當兵,就要寫小說,留下了白紙黑字,悲劇就在這裡發生,今天只要提到皇民化運動,幾個特定的作家就會被拿出來檢討,例如陳火泉、周金波。但是,那些到前線作戰的台灣人,沒有留下任何紀錄,好不容易在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裡提到一批台灣兵到中國作戰被俘虜,就是在說這個事件。所以,每一次在文學史課堂上,或者寫《台灣新文學史》的時候,談到這群作家,都會替他們感到悲傷,只因為他們留下了紀錄,就成為譴責皇民化運動的攻擊標靶,大家卻忽略當時整個台灣都認同日本。
接下來,我要談的故事,對我衝擊非常大,想在這裡與大家分享。有兩位赴日留學的優秀台灣醫生:葉盛吉與楊威里,在日本統治下,始終認同自己是日本人的身分,戰爭時期也非常擁護日本的國策。直到日本戰敗後,收到美軍拋下的傳單,才驚覺自己是中國人,於是商量好一同歸國。葉盛吉回台後,決定傾力為台灣社會服務,楊威里卻認為,既然我們是中國人,何不前往中國?
不久,台灣爆發「二二八事件」,楊威里在北京,還不知情,葉盛吉卻親眼見到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士兵開槍掃射,受傷的民眾全數送往當時他正在實習的台大醫院,他感到非常憤怒,轉而參加台灣地下共產黨。故事本來在這裡應該結束,但人皆無法預知未來,一九五二年葉盛吉被逮捕,彼時他已婚,知道妻子已經懷孕,因此提早將遺言抄寫在一本《聖經》中,並替孩子命名,寫下許多鼓勵孩子的話語。他告訴妻子,如果是男孩,取名為「光毅」,男孩出生後一個禮拜,他就被槍決了,妻子最後也改嫁了。故事回到楊威里,他到北京後,加入謝雪紅組織的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」;不過,謝雪紅發現,北京的共產黨對台灣人非常不友善,認為他們都是漢奸,因此不斷向毛澤東據理力爭,最後卻在一九五二年被清算。楊威里正是因為加入謝雪紅的團體,連續三次鬥爭都無法倖免,感嘆自己在中國有志難伸,如果當初與葉盛吉留在台灣該有多好。直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,在英國讀書的女兒寫信給楊威里,告知他中國外省的軍隊與北京的軍隊可能會發生內戰,應該趕緊逃出。楊威里經過國共內戰的摧殘,十分懼怕,馬上申請探親;臨走前,爐灶、桌子上的家當都還安放著,並且與鄰居說明這只是為期一個禮拜的探親,最後卻是一去永遠不回頭的決定。到了倫敦,他一句英語也不會,一九九○年便移居日本;一到日本的首要工作,即是尋找葉盛吉的下落,足足找了一年,才有朋友赴日告訴他,人已經尋到了,但是已經在一九五二年因參加地下共產黨而被槍決。楊威里一聽到消息,第一句話是:「ばか」(混蛋),他自己迢迢千里,在中國被共產黨欺負了一輩子,葉盛吉卻在台灣參加地下共產黨,歷史多麼的嘲弄人啊!為此,一九九一年楊威里決定回到台灣,拜訪已經改嫁的葉盛吉之妻,葉妻見著他,立即掉下眼淚,楊威里疑惑兩人從未見面,怎麼對方情緒如此激動?原來葉盛吉死後留下三十二本日記,幾乎每一則都提到與摯友楊威里相處、成長的過往。
後來,楊威里將日記帶走,寫了一本葉盛吉傳記,書名為《一個台灣知識份子的命運》,副標為「夾在台灣與日本之間的現代人」。早在這本書一九九六年在台灣出版前,我就讀到了日文版的《葉盛吉傳》,書籍出版後,成功大學邀請我談白色恐怖,演講中,我也講了葉盛吉與楊威里的故事。演講結束後,一名老年人與年輕人向前和我打招呼,老人說:「謝謝你今天告訴我們台灣過去的歷史,我叫楊威里。」年輕人則點頭稱道:「是的,陳教授,謝謝你,我叫葉光毅。」我所談的五十年代遙遠的歷史、遙遠的人物,竟然一下子跑到我的面前,至今我講起來仍舊雞皮疙瘩直冒。原來,葉光毅本來想赴美留學,卻為了要看懂父親留下的日記,改赴日本學理工,拿到了博士學位後,回到台灣成大教書。楊威里剛好那天去拜訪葉光毅,在海報上看到陳芳明要談白色恐怖,就相約來聽。歷史就是如此狹窄,並非我們想像的廣大,我就在那一年,經歷了和歷史人物這樣相遇、交錯而過的奇妙經驗。
夢的轉向:文學是我的志業
我今天談這些,究竟與我的文學夢有什麼關係?其實關係太大了。我必須了解台灣的命運如何造成。難道台灣沒有歷史,沒有文學嗎?我過去所受的教育訓練中,從來沒有接觸台灣史的機會,課程中完全沒有台灣史這門課,台灣自然被關在思考之外。我對台灣歷史產生興趣,開始於美加國境被阻擾的遭遇,疑問自己的家國究竟在何方?然後帶著慚愧的心逐步整理台灣歷史,連帶著閱讀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。
一九七九年「美麗島事件」發生的那年,我第一次閱讀賴和的小說。過去從來沒有聽過賴和這個作家,只有一九七七年《夏潮》雜誌,梁景峰寫了一篇文章〈賴和是誰?〉,是的,究竟賴和是誰?為什麼過去我們沒有這樣的記憶?完全是因為台灣的教育將之排除在外。我首次讀賴和小說,感到非常惆悵,原因是他的文字又像日文,又像白話文,又像台語,這種混融的語言乍看之下簡直不忍卒睹。但是,放下作品後,我突然想到,賴和的時代是沒有白話文運動的殖民地時代,寫這樣的小說其中一定有微言大義,於是又重新讀了一次。這也是我常常提的,閱讀從來不是一見鍾情,而是多看一眼,正如與情人相遇一般;我的文學之路,也是這樣開始的,當我第一次閱讀感到不忍卒睹時,就會重新讀一遍,理解作者為什麼那樣書寫。賴和的技巧不好,但是對日本強權的抵抗與批判,我慢慢讀了出來,最後把他擺到一個重要的位子。從他開始之後的作家,包括楊逵、龍瑛宗、呂赫若,我一本一本讀下來,台灣的形象第一次那麼清楚地出現在我的思考裡,過了半生,旅行了半個地球,快要三十歲,才發現台灣。台灣對我來說,是門遲到的學問,但可以慢慢追趕,這也是我後來偏離了過去所做的宋代研究,迎向台灣文學史研究的原因。
一九九○年,我在海外寫了台灣共產黨領袖傳記《謝雪紅評傳》。伴隨著這段歷史的研究,我也把同時代的文學讀了一遍,這才明白,台灣文學實在太豐富了。雖然多半用日語寫,但我們都知道,他們的靈魂是屬於這塊土地。呂赫若在一九三五年寫的〈牛車〉,是台灣日據時代寫農村寫得最美的一篇小說;該年為日本統治台灣四十周年,日本帝國在台北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台灣博覽會,向全世界宣揚帝國在短短四十年間,將落後的台灣轉變成現代化,而他們也有力量,將現代化推展向全亞洲。來台同慶博覽會的人很多,其中最重要的陳儀,就曾經在一次公開演說中,讚揚日本現代化的殖民成功,一九四五年他來台擔任行政長官,於松山機場演講時,卻稱台灣過去五十年受的是日本奴化教育,兩相對照,使台灣人感到憤怒與受傷。呂赫若馬上在《新生報》寫了一篇文章批判,為什麼陳儀赴日留學是現代化,台灣人受日本統治就是奴化?歷史果真嘲弄人,陳儀在一九三五年發言時,絕對沒有想到自己十年後會來接收台灣。
另一個例子,就是曾經參加農民運動,卻因為派系鬥爭而退出的楊逵。我們雖然失去了一位優秀的農民運動者,卻得到了傑出的作家。一九三二年楊逵寫了《送報伕》,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,他認為台灣作家應該站出來寫作,不應該繼續沉默,便在一九四八年《新生報》發表了〈我們應該重建台灣文學〉。當他提到「台灣文學」後,馬上被圍剿,攻擊者認為,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,因而產生了一系列論戰。一九四九年,楊逵又發表了〈和平宣言〉,希望本省、外省人共同將台灣建設起來,國共內戰也不要將台灣捲入;這篇六百餘字的文章,使他被軍政府約談,他以為這樣的文章只會被關一天,不料一關卻是十二年,直到一九六一年才被放出來,這時整個台灣社會早已改變。這樣一個作家,被放出來以後,依舊老老實實安居在東海大學對面的亂葬崗,開闢了「東海花園」。
在這裡發生了一個精采的故事:東海大學思想史教授徐復觀,每每在學校附近散步,總會見到墓園中澆花的鄉下老人,好奇心使然,便走上前去試著以日語打招呼;沒想到楊逵以極典雅的日文回禮,徐復觀知道對方一定受過教育,就應邀到楊逵的違建木屋中談天。一進到屋中,徐復觀驚嘆滿牆的資本論等社會主義相關日文書籍,才明白台灣民間太多臥虎藏龍的素人。楊逵去世後,徐復觀將這個故事告訴胡秋原,胡氏便寫了一篇〈進步台灣,落後中國──紀念楊逵〉。我就是在先人身上,看到他們一輩子都在努力,即使在如此艱困的環境,看不到希望的時代中,他們的信仰卻永遠不會屈服;對我來說,這是非常重要的召喚。如果先輩在看不到希望的時局中,都能奮鬥不懈,在這個看得見希望的世代,我能夠不努力嗎?因此,我慢慢思考台灣人文的問題。
作為一個海外的流亡者,以及政治立場為綠色的讀書人,我曾經相信那個政黨與那個政治夢,決定去實踐它,走過一遭之後,才發現政治不是我終身的職志。離開民進黨之前,施明德問我未來的規劃,聽到我要去教書先是肅然起敬,但聽到是靜宜大學的講師,卻開始表現出痛失英才的樣子,告誡我已經四十八歲了,難道還要從講師開始當起?接下來就要規劃你當不分區立委了呀!我告訴他我真的喜歡教書,這也是我毅然決然離開政治的原因。如果,我繼續在政治圈待下去,最大的成就,應該就是在立法院打架吧!台灣社會需要一個打架的立委,還是能夠研究台灣文學的學者?一九九五年,我在靜宜大學開的第一門課,就是台灣文學史;當時全台灣還無人開這樣的課,但是,教學相長,不學便無以教學生,教了以後反而可以學更多,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,我開始寫台灣文學史。
正如前面所言,我開始認識台灣,是在海外旅行了半生以後;但是,真正融入台灣,反而不是在政治場域,而是在教書以後。我的散文集《夢的終點》,談的正是我在海外一直作著一個在台灣製造革命的夢,回到台灣以後,才發現台灣已經有新的建設,經濟發達,中產階級誕生,還能革什麼樣的命呢?所以,夢的終點,寫的正是革命夢碎,我向自己說,你就老老實實地在這塊土地上活下去,關心台灣社會。作為一個學者,所擁有的知識,應該不只是用在校園中,而是用行動來干涉權力與社會吧!進入學殿以後,我告誡自己,不要當一個有潔癖的學者,該發言的時候,就應該發言,不要顧慮自己是什麼顏色。也就是這樣的性格,在二○○六年爆發國務機要費案時,眼見好幾個世代人投入而造就的民主之夢破滅,我寫了第一篇批判的文章〈誰還記得清廉、勤政、愛鄉土?〉,卻在一夜之間失去所有朋友。即使如此,我知道一個夢的實現不是依賴辯論,而是每一個世代的人去實踐;而這個人就這樣把所有的夢都出賣,不僅僅是民主改革的丟臉,也使台灣在國際上失掉了尊嚴。我問自己,作為一個知識分子,即便失去了所有朋友,我還要不要繼續寫下去?還要不要勇敢地向權力中心講真話?答案是肯定的。
台灣新文學史與文學夢的展望
經過這樣重大的衝擊與危機,二○○八年政黨輪替時,我忍住了,埋首將《台灣新文學史》寫出來。寫這本文學史,不只是留下台灣過去最佳的心靈,也希望文學史不只是一個人在寫。台灣文學如此豐富,我讀了一輩子作品,也才寫出這麼一本文學史,很多人不滿自己沒有被放進去,卻不去關心我在解釋每個時代的藝術成就,是否有謬誤之處?或者是,這些人能不能撐起如此美好的時代?台灣文學史寫的是當代歷史,當代本來都是一直在流動、生長的;被我寫進去的年輕
人,也許十年後就停止創作,我當然會持續改寫,當代史永遠都是在改變的,要用動態的觀點觀之。
因此,歷史應該由很多人共同創作,產生不同的版本進行比較,才會完整,也才是寫歷史正確的態度。因為這樣,我認為作為一個歷史書寫者,成就並不會很高,作家才能跨越時代,好的作品會一代一代的傳下去。一九六○年代作家所創作的作品,現在都已經變成經典,經得起時間的考驗。最後,我要說出最後一個夢,如果上天眷顧,我希望自己能夠成為小說家,寫出這一生所看過的故事,遭遇過的經驗,所聽來的傳說,成為當代歷史記憶的紀錄者,也希望在座各位成為我的讀者。
真的,只要夢還存在,想像就不會滅亡。
上述內容為陳芳明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,自述文學夢追尋過往,2012年於紀州庵文學森林辦理之《我們的文學夢》。
還想進一步聽芳明老師分享他對台灣文學的探索,可以把握2020年11月07日周六1400-1600起,陳芳明將帶領讀者細細品讀每位詩人的語言運用與風格塑造,相關課程資訊詳見下表:
上課地點:紀州庵文學森林(台北市中正區同安街107號,近捷運古亭站2號出口)
每周六1400-1600,共12講
繳款資訊
線上登錄課堂報名資訊後,尚須完成繳款(3天內),經承辦人員確認款項收訖後,才算完成報名喔!
●繳費後請回傳
1.姓名2.匯款帳戶後五碼3.匯款金額4.匯款日期,至hsuyuyin@kishuan.org.tw,俾利為您對帳確認
●繳費方式:
1.銀行匯款
戶名: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市定古蹟紀州庵及新館營運管理處
銀行別及分行別:台北富邦銀行-城中分行
銀行及分行代號:012-7314
帳號:731-102-006679
(於上課時發放發票)
2.ATM轉帳
銀行代號:012 帳號:731-102-006679 (於上課時發放發票)
注意事項:
1. 如為候補學員,請務必收到轉為正取人員電話或EMAIL通知後付款
2.課前一週將寄發以信件寄發開課通知,請留意相關訊息
3. 課程繳費後取消與退費:
1.開課日前7日退費(全額退費),並扣除匯款手續費。
2.開課日前1~7日內退費(退費80%),並扣除匯款手續費。
3.開課日後,未逾全期活動/課程1/3(退費50%),並扣除匯款手續費。
4.特殊專案課程退費辦法另訂之。
主辦單位: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X 紀州庵文學森林
協辦單位:文訊雜誌社
指導單位:文化部 台北市文化局